|
【内容提要】 “人总是追求幸福”。在许多道德哲学的视野里,这一判断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的宿命,人的天性。如果从人类总体来看,我们能够相信上述命题的真理性。因为追求幸福是人类作为一个族类总体的终极目标。正是这一终极目标,激发出人类改造世界的无限激情,牵引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与发展。那么,当人们面对当今社会结构之转型、市场经济之发展、金融危机之威胁、精神家园之安顿时,“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也凸显了出来。 【关键词】 自然生态 幸福观 鄂托克
一、幸福的理性之维 由于理性是人类存在的灵魂,因此,只有在理性存在的维度上才有幸福的生成。没有理性的引导,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活动(包括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即不仅意味着不可能形成真理,而且意味着不可能有合理的行动。而人的幸福只能存在于合理的活动之中,即存在于以理性为引导的活动中。因为合理的活动即是合于规律或必然,是人的本质所在,所以能够生成幸福,而不合理性或反理性即是不合规律或必然,因而不可能生成幸福。由此来看,历史上的理性幸福论抓住了幸福的根本维度。幸福不是生活主体自我的强势,并不是自我强占式欲望的满足,而是回归心灵深处自我的一种安静、包容、自省。也包括与“他者”情境的和谐共处与融通。 人类从类人猿产生,即是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飞跃。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超越自身自然状态的历史,是社会性不断扩大不断加强的历史,是人类仍然遗留的某些自然状态不断减弱的历史。于是,人类似乎认为我们是在理性指导之下,表现出了自然万物面前的一种强势。传统意义中,人类往往是将理性的中心归于自我,而将“他者”视为理性的对象。当这样的理性方式强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我所谓的幸福之感是主体对象的强占与自我欲望不断地满足。意味着幸福是一种“所欲”。那么,“所欲”何为?这必然要指向一个外在的对象,是一种对符号化、间接化、抽象化、解构化的精神向往。似乎人类这时体会到人之精神的伟大,也似乎看到人类精神幸福的真正蕴意。当然,此时我们也会看到“极端式”自我虚幻精神幻想的那头,是人类将自己比划为宇宙万物的中心,无限的极端自我精神幻想刺激带动着物欲无限的扩张。当“上帝已死”的号角吹响的时候,人类再没有想到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东西。“理性”似乎成为人类能力的代名词。于是,一切“他者”对象都成为自我的一种工具存在方式。在“他者”与自我对立的境况下,“他者”既包括物的世界、他人也包括“自我”。一切都以对象而存在,一切都可能成为他者的工具。所以,当理性成为工具的一种状态时候,我们会看到,人类其实处于一种物化的状态之下,最终在人的观念之中物欲被无限扩张,似乎从表面看来人是万物主宰,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物最终成为了人类的主宰,有着对人无条件的支配性和主宰权。马克思曾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来描述这种人的生存状态,认为在这种状态中,“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1}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却最终还原为“物的价值”,人沦为“物化”的存在,成为物的手段和工具。从“我”的角度来讲,也意味着自我的“异化”,看似强势的自我,却完全被工具化的理性丧失本我的完整价值。此时,在丰富的物质欲望被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常常问自己,我到底是谁?甚至,将此作为向他者宣扬的资本。从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存环境而言,一切存在的环境都是“低人一等”,都是作为满足人类欲望而存在,工具理性思维决定了人类只会对局部自然对象的思考。所以,我们在看清规律的同时,却破坏了自然整体的规律。无极限的开发与发掘必然造成自然生态的灭绝性的破坏。当人们在为滇池开发沾沾自喜,为蝇头小利眉开眼笑的时候,生态破坏的代价却远远超过了开发带来的利润。所以,在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幸福生活中,人类只能沦为“物化”的生活状态,何谈幸福之有? 由此看来,传统的理性是以工具理性为核心价值,由此形成的幸福并没有抓住幸福的根本维度。那么,何种理性才能引导人们真正的幸福呢?理性的存在并不是以解构、分析某个对象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一个整体的维度,最终还要回归到一种价值应然的关系之中。人与“他者”情境是一种对等的关系,甚至是对“他者”情境的一种敬畏、感恩关系。对于人自我而言,什么是真正的我,在生活的世界中如何找回自我,这也是幸福生活的最终目的归属。当理性的生活并不再以工具为核心指导价值,而是从我与“他者”对等的一种关系角度出发的时候。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幸福观不仅仅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幸福态度。从哲学史上看,有关天性的解释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神学的,一种是哲学自然主义的。在神学上,天性的基本底蕴是上帝给予或神授的;在哲学上,天性指向的是大自然的造化。我们可以将理性的幸福建构在一种被“给予”的层面上,人类对“他者”存在的敬畏,将“他者”放在神的位置,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柔弱,也不意味着一种愚昧。而是将人类自我视同于自然万物的存在,承认自我能力的有限性,也承认自我存在的“部分性”。只有这样,我们的心灵才能融合于“他者”的情境之中,幸福才能寓意于“他者”的情境之中。我们才能从内心深处感恩自然,修行于自我,也就能体会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人与自然共融一体的幸福意境。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同意动物的趋利避害与自我保存的倾向为天性,因为那是纯粹自然进化的结果,但却不能同意人对幸福追求的激情为天性。深刻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就人的幸福感的获得还是就人追求幸福能力的进化来说,不能视之为纯粹的自然进化的结果。动物没有幸福的问题,幸福的问题是专属于人的,只有人才有幸福的问题。动物的趋利避害与自我保存是一种由自然进化所形成的本能,它不关涉价值或意义问题,而人对幸福的追求则蕴含着一种价值取向。从人类自我来说,理性的幸福并不排除感性的满足,而是理性引导的活动过程中的理性的愉悦,是以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为基础的理性指导。只有在这样的理性引导下的活动才是合理的活动。“人是目的”是人类幸福理性活动的最终价值指向,人成为“价值主体”,“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必须服从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的目的”。{2}遵守“每个人都应被视为目的”这一“绝对命令”,所组成的将是一个人与人互为目的的“目的王国”,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成为这一目的王国的成员,并且“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3}因此,这样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最高形态的幸福。 二、理性幸福与草原文化 鄂托克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位于鄂尔多斯市西部,东邻乌审旗,西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乌海市交界,南与鄂托克前旗连接,北与杭锦旗毗邻,西北接乌海市。全旗南北长209公里,东西宽188公里,总面积约20687平方公里。鄂托克旗历来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生息之地。“鄂托克”一词系蒙古语,汉译为“营”或“部”,是元、明两朝蒙古“万户”下的行政建制名称,即“千户”。清顺治六年(1649),朝廷将鄂尔多斯右翼诸“鄂托克”中的克扣特、锡巴固沁、乌喇特、塘沽特等蒙古部划为一旗,称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新中国成立后,称鄂托克旗。目前,鄂托克旗下辖4个苏木、2个乡、6个镇和9个居民委员会。乌兰镇为旗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旗政治文化中心。鄂托克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历史悠久的畜牧业大旗。畜牧业是鄂托克旗的主体经济。历史上曾以“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著称。也正是鄂托克旗这种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产业结构决定了鄂托克旗是以草原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它的幸福观除了具有一系列独特自然性外,同时还体现在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之中。当工业文化处于当今世界的主要角色的时候,鄂托克旗的幸福观是对工业文化中工具理性价值的反思,超越了工具理性价值,将理性放在了以自然为平台这一背景之中。真正理性是对工具理性的反思,是一种整体背景,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幸福方可不被异化。 鄂托克旗幸福自然观正是草原文化中一种内在的回归自然、追求朴素的生态幸福观。它明确指出天地自然是人及万物之生命的本源。天地自然先于人及万物而产生,人及万物以天地自然的存在为前提,也是幸福自然观的本原之地。所以,对自然的崇尚无不充实在鄂托克旗幸福观当中。在长期的游牧生产中,游牧蒙古人领悟到人与天地万物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宇宙(“遨日其朗”)统一整体中,相互间密不可分;世上万物都是天父地母所生,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赖以生存的摇篮,遂形成了“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的自然本体价值。把天与地视为万物之源,人类万物有赖于天地而生,是游牧蒙古族对人与自然关系最古老的认识。这种质朴的自然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导致草原游牧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归顺自然、依赖自然、适度师法自然的观念。在游牧蒙古人的心目中,由于大自然的地位至高无上,因而,对自然不仅依赖,更是信仰崇拜,赋予大自然、天与地以神性。这种仰拜的意识和情愫在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们崇拜的对象一般都是灵化了的自然物、自然力及一些自然现象,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树神、动物神、祖先神……认为这些自然物、自然力及一些自然现象皆由神灵主宰。草原的兴旺、五畜的平安都有赖这些神灵的保佑。从“依赖”到“崇拜”,体现了人从大自然恩惠的接受者到自然界的尊崇者的角色转换。正是在“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的自然本体价值意识导向下,他们不仅要崇拜自然,进而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赖以依存的自然界,爱山、爱水、爱草、爱树、爱原野上自生的牲畜(野生动物),用诚实的心灵和自觉的行动回报大自然的恩泽。进而去用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词语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来赞誉他们最熟悉的大自然。比如他们对阿尔泰山的美誉:“……辽阔无边,坚如磐石/富饶的阿尔泰山啊,永远繁茂/……/辽阔无边,高耸云端/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的摇篮/……/辽阔无边,坚实雄伟/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祖先的天堂/……/辽阔无比,雄伟秀丽/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的骄傲/……辽阔无比,雄伟入云霄/富饶的阿尔泰山啊,我们人生的晨晓/……辽阔无比,矗立在蒙古大地/富饶的阿尔泰山啊,还是那样美好/……”{4} 自然生态的幸福观是鄂托克旗人对自然的崇尚、感恩以及赞美之情的抒发。也正是这种自然生态的幸福观孕育着鄂托克旗人那种诚实守信、坚毅勇敢以及豁达好客的情感特征。游牧民族以蓝天为盖,以大地为床,以毡庐为住,以马驼为行,以敖包为祭,以长调为歌,这种天然的文化本性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保持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单纯质朴。同时,为了共同的生存,游牧民族必须团结在一起,所以诚实守信成为最高的道德水准。如蒙古族曾有谚语:“真诚是万美之根,虚假是万恶之源”、“获得别人的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的错误凭真诚”、“宁可失良驹,切勿失诺言”等闪光的格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游牧民族弘扬诚实和信任良好传统的有力说明。{5}在长期的牧猎过程中,恶劣多变的气候、险恶的生存环境、为避免野兽和外族的侵袭以及为争夺草场所进行的征战等等,造就了游牧民族强韧的体魄和所向披靡的精神气概,形成了勇武、无畏、豪放、进取的尚武特性。在长期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游牧社会中的所有成年男子都是战士,游牧行猎“不单是为了猎取野兽,也是为了习惯于狩猎锻炼,熟悉了马刀和吃苦耐劳”(《世界征服者史》),所以几乎是全民皆兵。《史记》中有文字记载“宽则随畜以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随时准备迎接外来的武力进攻。在这种尚武精神的传承下,形成了游牧民族独特的战争观和生死观。在他们眼中,战争犹如一场竞赛或游戏,有赢有输,有死有生,荣誉比生命更为重要。虽然过强的流动性使文化的积累性较差,很难形成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但流动性有利于游牧民族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相互交流,对任何外来事物都不排斥,广泛接纳各种文化,对各种外来文化都能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体现了草原文化的开放性。游牧民族热情好客,远来的都是客,以客为尊,不论认识与否,不论尊卑,都要嘘寒问暖,递送茶酒,热情接待。比如蒙古族遇到客人或路见行人,都要问好,并邀请至蒙古包做客。成吉思汗曾在《大札撒》中规定:“行路时经过用餐人的旁边,可下马与之共席用餐,用餐人不能拒绝。”{6}传说一个孩童问母亲,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游牧和迁徙,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母亲告诉他:如果在一个地方定居,额吐根(萨满教中的地母神)会疼痛的。只有当蒙古人游牧和迁徙时,就像地母神的血液一样在她身上流淌,才使她感到舒畅。牧人的这种善待生物、善待其他所有和人一样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的自然观,与所有存在为善的情愫,充分表明了草原牧人对大自然的无限关爱,最终是真正更好地善待人类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人民出版社,1971。 {2}{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敖其尔巴图等:蒙古民间文学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 {5}马桂英:略论草原文化的特征[J]天府新论,2006(1)。 {6}台湾蒙藏委员会:蒙古族民俗[M]台北,1999:51。
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讲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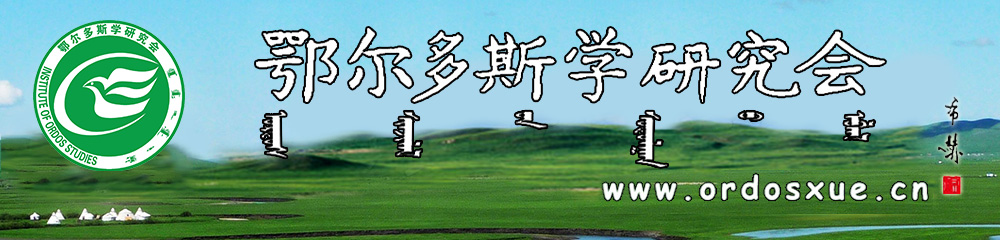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