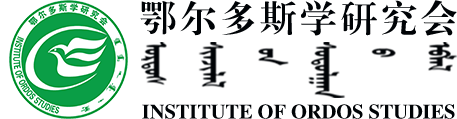整个1960年,是在下放劳动锻炼中度过的。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干部轮流下乡、上山(后来为顺口,一律称为“上山下乡”)。盟财贸系统抽调约20名干部,连同系统内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分为三个小组,到大树湾大队(当时为树村召公社的二大队)的三个小队劳动锻炼。上级规定,每人全年必须挣够二千工分,业余时间帮助社员学习文件,辅导扫盲班、管理食堂,协助农技学习班。我当时年青力壮,样样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年底,中央下达公开信,即“十二条”,反对“五风”,放宽政策,让广大社员休养生息,以恢复农业生产力。中央这一文件,受到干部群众热烈欢迎。第二年(1961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粮食产量都大有提高。我们深切体会到,政通人和比风调雨顺更重要。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下放劳动加上参加整风整社一年多,我加入了共青团。回单位不久又被选为团支部委员。但因为下放,我失去了或者说大大推迟了上大学的机会。1960年高校招生数比高中应届毕业生还多,许多在职人员顺势升学了。我1961年从达旗完成整社任务回来获准参加高考,然而,同上一年相比,形势陡变,高校招生规模大大压缩,而且基本不收“调干”。于是,我只有望大学兴叹的份儿了。
1961年雨水充沛,滩上、梁外,一派丰收景象。秋天,我被抽去参加秋收劳动,地点是鄂托克旗公卡汉公社。一望无边的糜子田,甩开膀子干了半个多月。那一年,虽然全盟粮食仍然没有“过关”,但压力大大缓解。从鄂旗回来到六一年年底,加上六二年一整年,算是在本职岗位的港湾里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到1963年,又“外放”了,而且从此之后就以中心工作为主,以银行工作为辅了,再也没有煞下心来搞过金融业务。
先是“四清”,派到达旗王爱召公社。队长是李文高,何有义、卓力克,如今全都过世了。一起工作的还有达旗十多位部门领导,新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次年春天转到树林召公社,与旗委领导刘占江、宣传部干事甘英才等接触不少,与达旗以及树林召公社的干部门都混得很熟。亲身体会到“文革”前夕那场运动,政策越来越左,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我自认为头脑比较清醒,不肯参与那左的竞赛。期间还就社队“四不清”干部退赔减免问题写过一份报告,报了上去,估计也没起什么作用,因为1964年冬天起,形势就更加紧张和严酷了。
接下来的1965年,全盟大旱,赤地千里。我被盟“抗办”分配到驻包抢运组,在刘羊焕、胡其铭等人领导下,为灾区人民抢运粮、草和各种救灾物资。那一段特别繁忙,身兼秘书、会计、编辑、联络数职,然而苦的值得,累的愉快。总比违心地宣传二十三条,对自己熟悉的社队干部大张挞伐心安理得多了。救灾抢运一直搞到1966年秋天。一来救灾物资运得差不多了,二来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无缝对接”,我们抢运组的人们各自回到原工作单位。不久分别加入东胜地区的两大群众组织,各事其“主”,各逞其“狂”,如今回忆起来,荒诞、滑稽、苦涩、悔恨、惋惜,什么都有,真的是五味杂陈。